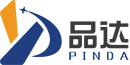生活频道发稿:分享日常,传递生活小确幸
晨光透过纱帘时,我正站在厨房案板前切香菇。刀锋与木砧板相触的笃笃声里,深褐色的伞盖裂成均匀的月牙,水珠顺着菌褶滚落,在晨光中折射出细碎的银点。这方寸之间的专注,总让我想起汪曾祺笔下那些会呼吸的文字,他说做饭是“对生活最本真的回归”。

砂锅里的水开始咕嘟冒泡时,手机屏幕亮起同事的语音消息。她抱怨着早高峰地铁的拥挤,背景音里混杂着报站广播。我望着窗外梧桐树影里摇晃的光斑,忽然觉得此刻能守着灶火,听着香菇在汤中舒展的轻响,何尝不是种奢侈。上周在旧书市淘来的粗陶碗盛满热汤时,蒸腾的雾气模糊了玻璃窗上的霜花,却让记忆里某个相似的冬日黄昏愈发清晰——那时母亲也是这样煨着汤,任时光在氤氲的香气里缓慢流淌。
.jpg)
午后整理书架,翻出夹在《人间草木》里的银杏叶书签。去年深秋和友人同游植物园,金黄的落叶铺就通往温室的甬道,我们在热带蕨类植物丛中发现株含苞的昙花。当时笑说定要熬夜守候花开,结果各自被琐事牵绊,终究错过了那刹那的芳华。如今干枯的叶脉仍保持着完美的扇形,倒像是把未竟的约定拓印成了永恒。
暮色渐浓时,楼下的腊梅开了。裹着围巾经过石桥,看见独居的张奶奶正在给流浪猫布置纸箱窝。她佝偻着背往泡沫箱里塞旧毛毯,白发间别着枚珍珠发卡,那是她女儿去年从上海寄来的生日礼物。寒风卷着细雪掠过水面,几只橘猫却挤作一团,尾巴尖轻轻拍打着人类善意的温度。这种不期而遇的温暖,总让人想起顾城那句“树枝想去撕裂天空,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”。
回到书桌前续写读书笔记,台灯将绿萝的影子投在素白墙面上,恍若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钢笔吸饱蓝墨水,在纸页间沙沙游走,忽然记起童年练字时父亲总说:“横要平,竖要直,就像做人。”那时不解其意,如今看着自己写下的横竖撇捺,倒品出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智慧。墨香混着茶几上佛手柑的气息,在暖气房里织就温柔的网。
睡前关掉所有电子设备,月光正好漫过窗棂。蜷缩在羽绒被里数心跳的节奏,恍惚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爆竹声。原来已是旧年将尽,新岁欲临。那些散落在日常褶皱里的吉光片羽,如同暗夜里闪烁的萤火虫,照亮我们走向春天的路。